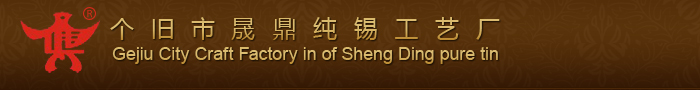红河哈尼梯田的守望者
发布时间:2014-06-24点击数:4877
感动:那些用脊梁挺起世界遗产的人

王力军教授(右一)在哈尼梯田现场工作
1999年冬,哥布、艾吉、李雄春、车明追、张红榛等红河哈尼梯田文学研究会的几个人,抱着刚刚出版的《梯田文化报》,迎着寒风,走在锡都个旧的街头,向行人散发。当期的报纸上,全文刊登了史军超有关哈尼梯田申遗的构想。他们于不知不觉中,走在了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漫漫长路上。
2000年,作为一名先行者,张红榛被调进了红河哈尼梯田申遗办公室。办公地点在个旧州政府食堂二楼,临时办公室略显拥挤,刚开始只有她一个人,后来增加至3人。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路走来那么艰苦。她用了整整13年,执著追寻在红河哈尼梯田的申遗路上。13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刹那,而对于人来说,却显得那么漫长。13年,张红榛基本不分什么节假日,只要工作需要,随时启程出差忙于申遗工作,工作状态也是生活状态;13年,她的女儿从小学,上到中学,上到了大学毕业。13年,她跑元阳,跑昆明,跑北京,为申遗而呼,走过的路已不计其远。13年,为了申遗业务,她陪同考察哈尼梯田的专家、学者,已不计其多。
也正因为此,她被人们尊敬地称为“梯田守望者”,对于那些热衷于梯田宣传和保护的专家,则被她称为“田亲家”,而她却自称为“大地母亲的女儿”。作为红河州哈尼梯田管理局的首任局长,作为从哀牢山云雾深处红河县走出来的普通哈尼妇女,从小生活在美景如画,震撼人心的红河南岸梯田山水间,她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和自己的民族,如同热爱自己的亲生母亲。
张洪康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头“老黄牛”,他将自己的网名定为“耕牛”,并自言“苦耕梯田,乐在其中”。2012年3月,元阳哈尼梯田核心区开始大规模环境整治,他与同事一起一头扎进工作中,直到7月才告捷而回。而此时,是元阳县最热的时候。
还有李贇立、周杰、小陈、小李、小杨等等,从最初的申遗办到后来的梯田管理局,从最初的一个人到10来个人的团队,申遗工作团队越来越充实,他们用奉献和坚持赢得了最后的成功。
不管是领导、办事员还是司机,每个人都为申遗倾尽心力。有一次,司机到昆明去接北京来的专家,因为天气原因,专家所搭乘的飞机晚点,直到凌晨时才到昆明。他们连夜赶到蒙自时,天已将亮,他们洗把脸,稍事休息一会,吃了早点,便赶去参加会议了。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在他们的记忆中,几乎已经没有节假日。在迎接哈尼梯田“大考”的日子里,他们每个人都在“连轴转”,可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也没有谁计较得失。他们推动着申遗工作一步步向前,为哈尼梯田走向世界凝聚正能量。
在哈尼梯田的申遗团队中,王力军所带领的规划团队一直走在前面。王力军,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教授,2008年,因为接受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规划编制,王力军第一次来到哈尼梯田。这是一个浓雾升腾的日子,他没有看到什么,但依然能感受到这个农耕社会的和谐。此后,在他的规划里,“和谐”一直是他追求的最高目标。他以最实际和最可行的方式,指导现在和未来哈尼梯田的管理,其中,最重要的是持续不断地注入农耕存在的动力,让人与自然的和谐充分展示。王力军说,他愿意成为延续哈尼梯田生命过程的一个志愿者。
申遗文本是提供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要件,中国遗产研究院的张谨博士,与她年轻的同伴们一起担起了这一重责。他们不分黑夜与白昼,不分节日与假日,将一份高质量的申遗文本如期交付。他们是带着深厚的“遗产感情”来书写文本的。申遗成功后,张谨仍十分关心哈尼梯田的未来,她专门撰文称:“哈尼梯田申遗成功,作为以农作为核心的活态遗产,她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对哈尼梯田的保护与管理,时刻不能放松,需要漫长而艰苦的坚持,更需要科学的研究决策。政府与公众都需要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保护当中去,才能形成长期有效的保护,才能实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
申遗路上,走来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感动的身影。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罗德胤,不顾天气炎热,为哈尼梯田核心区的整治洒下汗水。云南师范大学的角嫒梅,作为一个痴心研究梯田文化的专家,她对哈尼梯田潜心研究,成为申遗专家现场考察时向联合国专家汇报工作的专家组主汇报人之一。张维,云南出版集团的策划人,是他策划组织了丰富的梯田文化图书,打开了世人认识哈尼梯田的重要窗口。昆明电视台的周岳军,他守候梯田,用近20年的时间,一直关注、记录哈尼梯田,通过他的镜头,哈尼梯田精彩呈现于世人面前。
申遗路上,走来了一个又一个热心的志愿者。从美国一所著名大学毕业的王嵛,是一个醉心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个旧人。200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走上了哈尼梯田的申遗之路。她与红河州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在苏州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用流利的英语向国外专家热情介绍哈尼梯田。她当翻译,发资料,忙得不亦乐乎。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元阳箐口村的李兰、李阿文,也以志愿者的身份,用漂亮的民族服饰、优美的舞蹈、令人惊奇的哈尼山歌,向与会专家展示了哈尼梯田文化之美。
2013年6月22日,世界遗产大会在柬埔寨召开,将审议包括哈尼梯田在内的遗产名单。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王国慧,成了柬埔寨会议上红河代表团的热心志愿者。年过七旬的老贝玛朱小和,以自己的方式坚定地走在申遗之路上。值得记忆的还有红河州摄影家协会,提供了大量精美图片;红河州梯田协会,默默支持;北京可持续发展协会,编写梯田文化教材;在北京的哈尼人钱东丽为申遗多方协调联系;元阳、红河、绿春、金平等县的干部群众、文艺团体,及无法一一点出的那些为申遗呐喊、奔走、聚力的人,都值得历史铭记。
 经过多年的努力,保护梯田已成为大家的共识。记者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平静地说:申遗成功了固然是好事,但不管是否申遗,我们仍会理性地看待梯田、看护梯田,梯田终归是我们的家园,保护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经过多年的努力,保护梯田已成为大家的共识。记者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平静地说:申遗成功了固然是好事,但不管是否申遗,我们仍会理性地看待梯田、看护梯田,梯田终归是我们的家园,保护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哈尼梯田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绵延整个红河南岸的红河、元阳、绿春、金平等县,仅元阳县境内就有19万亩梯田,从山脚到山顶断断续续,蜿蜒迂回于千壑万岭之中,有的地方级数高达3000多级。可在10多年前,这样的奇观藏身深山之中不为太多人所知。从2000年开始,13年来,在相关专家和相关部门的申遗努力下,元阳梯田正从幕后走来台前——人们认识它的同时,也为它的壮美所震撼,更为修建梯田的哈尼人的智慧所折服。但在13年前,当申遗建议被提出时,还被当做笑话:就这些山上的稻田,能成为世界遗产吗?
经过多年的努力,保护梯田已成为大家的共识。记者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平静地说:申遗成功了固然是好事,但不管是否申遗,我们仍会理性地看待梯田、看护梯田,梯田终归是我们的家园,保护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法国人不谋而合的赞叹
藏于深山中的哈尼梯田第一次被外界知道,始于1993年。
1993年,第一次国际哈尼/阿卡文化研讨会期间,荷兰、日本、美国、英国、瑞典以及泰国和中国的100多位专家在参观过元阳哈尼梯田之后,甚为梯田景观的壮丽与哈尼文化的丰富所折服。此后,法国自由摄影人杨·拉马两度前来参观梯田,而他,也是第一位称哈尼梯田为“大地雕塑”的人;而第二个,是法国人类学家让·欧也纳。两个法国人对元阳哈尼梯田不谋而合的赞叹,使得“大地雕塑”成为元阳哈尼梯田的代名词而风行于世。
1999年,有专家建议,将哈尼梯田申报为世界遗产时,还是有很多领导、很多群众都不相信,他们不会相信也不敢相信,梯田还可以成为世界遗产。
2000年,红河州以“红河哈尼梯田”的名义启动了申遗工作,并于当年呈报省政府批准上报国家世界文化遗产管理部门。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博士、文化顾问白海思博士应红河州的邀请,前来观赏元阳梯田之后,“颇有微词”地表示:“你们的梯田可害苦了我,使得我两个星期都无法工作,因为我满脑子都是梯田!”
2001年,联合国世界遗产文化委员会主任报告官亨利·克莱尔博士参观元阳哈尼梯田后说:“英国人对一个突然出现的奇迹会用一个‘沃’来形容,而对你们的梯田,我要用3个‘沃’来形容,如果你们现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现在就投你们的票!”
此后的几年中,不断有中外的专家和学者访问元阳梯田,一句评价基本代表了大家的看法:“元阳哈尼梯田的价值,不亚于埃及金字塔。”
变更游戏规则后的淡定
2004年7月,哈尼梯田与吉林高句丽、河南殷墟、澳门历史文化建筑群、广东开平碉楼、福建土楼同时被中国政府列为申遗预备项目。一时间,红河州、元阳县的许多人,谈论的都是申遗就要成功的话题,谈起来都是神采飞扬。但因国家为确保高句丽、澳门历史文化建筑群等具有国际影响的项目能够申遗成功,于2006年12月对国内100多项申遗名单重新评估,哈尼梯田再次进入中国政府公布的35家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但也排在了并不靠前的位置。
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申报世界遗产的游戏规则进行了调整: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这对于具有5000年历史的又创造了大量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的中国来说,这一规则的改变就如同中国举重选手一样,要获得世界冠军不难,要获得国家冠军却是难上加难。
但规则的改变却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人们的心态变得平和了,不再躁动了。而对于哈尼梯田来说,则是从各个细节方面加深了对它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完善了对它的保护措施,从不同的行业提出了让其可持续发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