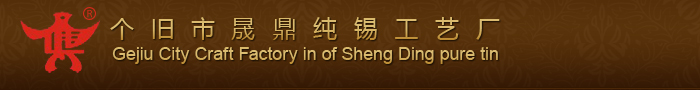梯田魂 美哉 壮哉
来源:红河日报发布时间:2013-12-08点击数:3277
梯田魂 美哉 壮哉
 哈尼梯田是世界农耕文明史上的奇迹,它呈现出的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良性农业生态系统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景观,正是21世纪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精神。梯田用水是从大沟中挖出无数分支水沟,分支水沟再通到块块梯田中,确保了每块梯田的灌溉。由于山水终年不断,哈尼人的梯田一年四季(除秋收后放干田水晒田的短时间)都注满了水,这水从上一层梯田流到下一层梯田,层层下注,最终又流回江河中,江河蒸发到森林,如此周而复始,永不中断。
哈尼梯田是世界农耕文明史上的奇迹,它呈现出的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良性农业生态系统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景观,正是21世纪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精神。梯田用水是从大沟中挖出无数分支水沟,分支水沟再通到块块梯田中,确保了每块梯田的灌溉。由于山水终年不断,哈尼人的梯田一年四季(除秋收后放干田水晒田的短时间)都注满了水,这水从上一层梯田流到下一层梯田,层层下注,最终又流回江河中,江河蒸发到森林,如此周而复始,永不中断。
生态密码:创造了“四度同构”的生态系统
现在元阳县有主干渠(大沟)4653条,截流了全县63958公顷原始森林和次生林中流淌出来的山泉、溪流、瀑布、龙潭水和雨季降落的大量山水,灌溉了境内166689亩梯田和147252亩早地,养活了元阳县36万人口。想要知道“元阳没有一座水库,17万亩梯田的水从哪里来?”答案就在这里。
哈尼人的水利灌溉系统体现了他们与哀牢山地理环境水乳交融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深度与广度在哈尼人居住的村寨设计中也同样展现出来。村寨,是哈尼人躯体和心灵温馨的栖居地,是他们家园的核心,他们在这里出生、成长和死亡,村寨的好坏关系到族群的兴衰。
哈尼人极其重视村寨的规划:村寨上方要矗立着茂密的森林,提供着水利、用材、薪炭之源,其中最神圣的是寨神林;村寨下方是层层的梯田,那里提供着哈尼人生存发展需要的粮食,村寨就设置在这二者之间。
为什么村寨要修建在梯田上方,水源下方呢?这里饱含着哈尼人高度的生命智慧和生活技巧。
因为梯田在大山上,哈尼人收获一粒稻谷要比平原地区的种田人多付出许多倍劳动量。一个平原上的人只要出了门径直走到田里去就可以开始干活,但哀牢山山高坡陡,哈尼人走出家门不是爬坡就是下坎,如果梯田在村寨上方,当人们爬坡上坎来到梯田边的时候,可能已经累得没法挖田了。村寨在上梯田在下,好处就是省力,即人类学家说的“缩短劳动半径”。
对种田人来说,水之外就是肥,“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有许多民族不懂这个道理,种“卫生田”。哈尼人却深知肥料的重要,极善植肥施肥。植肥是在梯田里撒浮萍让它自然成肥,所以春冬季节的哈尼梯田红红绿绿,长满浮萍,犹如织出的花毯。他们很早就懂得沤肥,把蒿枝、紫泽兰丢进田里沤泡成肥。最重要的是施厩肥和野放肥,为此,发明了独一无二的“沟水冲肥法”和“自然冲肥法”,毫不费力就把肥料送到梯田里。
沟水冲肥法哈尼话叫“则克机”,每个村寨都有一到几个宽大的公共积肥塘,牛马粪便污水都贮蓄在里面,经年累月,沤得乌黑发臭,成为高效农家肥,春耕时节挖开塘口,从大沟中放水把它冲入田中。这时的哈尼村寨像过节一样热闹,男女老幼纷纷出动,大家争先恐后用锄头、钉钯搅动黑糊糊的肥水,使其顺畅下淌,沿沟一路有人照料疏导,使肥水一滴不漏地冲入各家田中。
分田到户后,各家各户在房前屋后建起小积肥塘,平时堆沤畜肥,栽秧时节把肥料挑到附近的水沟边倒下去,肥料就顺水一路哗哗哗冲下去。施肥前只需打声招呼,沿途各家会自觉堵上水口,使肥料只冲入自家田中。比起平原地区的农民辛辛苦苦一担一挑地把肥料挑到田里,哈尼人真是高明多了。这样的施肥通常在栽秧前,肥料进田经过翻犁被压入田泥底层,变成了长效的底肥。
到了六七月间稻谷扬花抽穗需要施追肥时,哈尼人家已无畜肥可施,但是他们有“自然施肥法”解决问题。平时各家各户牛、马、猪、羊统统在山上野放,六七月雨水旺盛的季节,大雨自然会把满山遍野的畜粪、腐殖土冲刷下来,这时大沟又发挥了作用,把这些肥水悉数截入冲进梯田。哈尼人此时只需躲在自家的蘑菇房里吸烟筒,大自然已经帮他们完成了施追肥的劳动。
以水的流程为中心,经江边河坝蒸发升空,到高山区凝聚为云雾雨水洒落在森林中,化为山泉瀑布,又流入大沟,由水木刻分流入田,村寨在上,梯田在下,借沟水冲肥,层层梯田成为水的通道,最后水又归复江河。这是天地人三者相合的良性大循环,我将其归纳为“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
这就是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的构成原理,也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依据。哈尼梯田是中国梯田的杰出代表,是世界农耕文明史上的奇迹,它呈现出的良性农业生态系统和独特的梯田文化景观,它所蕴含的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发展的文化特征,正是21世纪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精神。
精神源泉:把梯田当琴弦弹奏生命之歌
梯田不仅是哈尼人的衣食父母,也是他们生活的魂魄,是精神源泉之所在。而那如银链般缠绕大山的条条水沟,那如布匹般包裹大山的道道梯田,正是哈尼人弹奏生命之歌的琴弦啊!
狂热的乡村音乐家——元阳县文化馆老馆长杨叔孔是我的朋友。20年前,他搜集到一首叫做《三弦啊,我的小飞马》的哈尼民歌,爱极了,经常对我引吭高歌:“三弦啊,我的小飞马,弹着你一道一道的琴弦,我的心飞到姑娘身边去了!梯田啊,我的小飞马,踏着你一道一道的田埂,我的心飞到天神摩咪的身边去了!”如歌中所唱,哈尼人是把一道道的梯田作为琴弦来弹奏生命之歌的。
他们对梯田,除了用锄头、犁耙和智慧、汗水,更是用生命来挖掘的。
1000多年前,哈尼人来到了哀牢山,他们所拥有的只是手中短柄的锄头和胸中万丈的豪情。但是,他们把生命的全部统统投放到挖梯田的劳作中,世世代代,从不休止,所以只有他们才能在陡崖上开梯田。
一个哈尼人如何把他的一生与梯田缠绕在一起,我们只要通过两个平常的习俗就可以知道了——
“哦哈都”,意思是“出门礼”。哈尼人的婴儿生下来,第13天才能抱出家门见天地万物,经过这个仪式,天神、地神、万物之神才会正式承认他生存的合法性并对其加以保护,这实际上是哈尼人获得生存权的神圣节日。但奇怪的是,这个仪式全部是指向梯田的。婴儿抱出来的时候,要在家门口立一柄三尖叉,上面挂一顶平时下田用的篾帽和一个挂包,如果是男孩,挂包里要放一把砍田埂用的弯刀;如果是女孩,挂包里就放一把割谷子用的锯镰,然后用3碗糯米饭献天神、地神。
“霍甲霍森森”,意思是“小娃娃开梯田”。这是一种儿童们经常玩的游戏,但它却有专门的玩法和道具。小娃娃们经常爱在自家门前或寨边空地上玩耍,他们每人都有一把小锄头,这种锄头的小巧玲珑跟一把汤勺差不多,当城市里的小孩在玩电动枪时,哈尼人的小娃娃却在用小锄头在地上模仿大人开梯田。
虽然是玩耍,他们和大人开梯田的程序是完全一样的。先开出水沟,还真的把水引进沟里,然后用泥巴筑起一层一层的迷你梯田,再把水引进梯田里去。他们干得非常卖力,不时用小锄头在田埂上拍拍打打,把它弄得滑溜溜的很好看。
实际上哈尼人对田埂的重视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比拟的,“糊田埂”是春耕时每个哈尼男人都要干的活。哈尼人说:田埂是哈尼男人的脸面,做得好田埂的男人,才能获得姑娘的芳心。长年累月,梯田在哈尼男人的手中轻巧起来,飘逸起来,变成了诗行,变成了水墨画。
大人们对小孩子玩开梯田的游戏总是给予鼓励,他们玩得满身泥垢的时候,大人就在旁边眯眼微笑,“梯田”开好后,大人会奖赏小孩每人一个红鸡蛋。这是男孩子的游戏;女孩子则各有一个小笆箩,她们会用小锄头在地上划出一些条条框框代表梯田,然后背着小笆箩在“梯田”里玩拿黄鳝、撮泥鳅的游戏,拿黄鳝、撮泥鳅是哈尼女人干的活儿。
所以,一个哈尼人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把他的命运和梯田联系在一起了,此后他生命的每一程都与梯田为伴——小时候在梯田边游戏;长大后在田棚里谈情说爱;结婚时新娘的穿戴是田间劳动的基本装备蓑衣、篾帽。总之,哈尼人的一生都投放在梯田里了,直到去世,他的坟墓也在梯田边,以便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守望梯田。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比哈尼人更钟情于梯田。他们把所有的欢乐和痛苦都给了梯田,祖祖辈辈,世世代代,无休无止,直到他们把座架哀牢山全部用梯田铺满,包括那些陡峭的山崖。
爱恋产生智慧,哈尼人在崇山峻岭间挖水沟可以证明这一点。水沟,是梯田的命脉,所以只要有水的地方,哈尼人必然要去挖水沟,不管这需要跨越山涧,还是凿开岩石。清代嘉庆《临安府志》里记载,哈尼人到了“水源高者,通以略勺,数里不绝”。就是遇到深涧老箐,就用竹子、棕树这些长直的木材挖成水槽,凌空架起来引水。有时这样的水槽可以绵延数里不间断。
梯田不仅是哈尼人的衣食父母,也是他们生活的魂魄,是精神的源泉。我以为,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将梯田当作艺术品来盘弄的。他们为此倾注的心血、力气和技能并不少于艺术家;他们将梯田视为自己的生命,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梯田。
大山是梯田的家,蘑菇房是稻谷的家。哈尼人从村寨进入梯田,稻谷从梯田回到蘑菇房。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也最动人的来往;而那如银链般缠绕大山的条条水沟,那如布匹般包裹大山的道道梯田,正是哈尼人弹奏生命之歌的琴弦啊!
哈尼梯田是多彩的大地艺术,而实现这一人类创造力、意志力和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哈尼人,则被誉为“大地雕刻师”;“哈尼梯田是真正的大地雕塑,而哈尼人是真正的大地艺术家!”
文明圣树:把梯田当舞台祭祀天地万物
哈尼人把最高的祭祀献给代表寨神的神树,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森林就等于水源,就等于粮食,就等于种族的延续,没有森林就没有水,就不能进行梯田耕作,人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哈尼人的古歌唱道:“有好树就有好水,有好水就开得出好田,有好田就养得出好儿孙。”对哈尼人来说,人的命根子是梯田,梯田的命根子是水,水的命根子是树,他们早已把这一切完整地融入他们的生命和生活。
哈尼人说:“要种大田在山脚,要生娃娃在山腰,要祭寨神在山头。”哈尼人对村寨的环境条件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所有寨子的上方必须有一座山包,上面要有茂密的寨神林,这是哈尼族最主要的公共活动地和祭祀地。崇拜祭祀树木就是崇拜水源,这样也就是对生命之源的保护。
哈尼村寨的建构形成了完整的神林文化,由神树崇拜的物质方式和一套严格纷繁的宗教仪式组成。通常位于较高山头,总管周围几个村寨的“总神林”,位于村寨上方的寨神林,位于村寨左右的神树林,位于村寨下方的“镇压恶鬼林”和村外路边的“人鬼分界林”。
每年农历二月的第一个属龙日,哈尼人都要在一年里的这一天,清洁村寨和各家的门户,举行隆重而盛大的仪式,邀请他们尊敬的神灵——寨神,从大山里进入他们的村寨,进入他们的家庭,进入他们的生活,享受他们的供奉,和他们一起同欢共乐,保佑山寨和哈尼人的平安、富足和幸福。
哈尼族将这一年一度的特殊日子称为“昂玛突”,也就是“祭寨神”的意思。“昂玛突”的历法意义在于由冬季进入春节,冬季休闲结束,春播、春耕季节开始,各支系有不同的叫法和祭祀时间。
今年,在攀枝花乡的洞铺寨我见识了一场最完整的“祭寨神”活动。在寨子后山有一片茂密的森林,森林中有一片巨石环绕的空地,正中生长着一棵高大标直的栗树,这就是洞铺寨的寨神树。
领头的是朱小和。他刻意穿上新衣,包上平时很少包的包头,手握一把弩弓,上面缠着土布,里面包着尖刀。他威严地喝令跟在身后的几个年轻人杀猪、杀鸡、煮饭、献祭。
朱小和是名满元阳、红河、绿春、金平四县的大摩批,他的名字不但中国人类学家熟悉,在日本、美国、荷兰、泰国、缅甸、越南、老挝人类学界也广为人知,他演唱的几万行的哈尼族古歌《窝果策尼果》和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是哈尼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朱小和享有“摩批哈腊”的头衔,“摩批”是祭司,“哈腊”是老虎,这表示他是哈尼祭司中资格最高的人。祭寨神是哈尼族最盛大的宗教盛典,这样的场合只有他才能主持。他端严地率领着徒弟们跪在寨神树下向寨神祷告。
哈尼人信奉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对天、地、风、云、山川、树、石、一草一木都要祭祀,在“天神的儿子”这个自称里,包含着哈尼人对代表大自然的神灵的敬畏与亲近。大树作为森林的代表,也许被世界许多民族崇拜,但没有哪一个民族像哈尼族这样,把大树作为一个族群命脉的精神和物质的至高无上的图腾对象加以崇拜。
哈尼人把最高的祭祀献给代表寨神的神树,是因为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在哀牢山这一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唯一能给他们提供生活用水和梯田用水的就是森林,森林就等于水源,就等于粮食,就等于种族的延续,没有森林就没有水,就不能进行梯田耕作,人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他们必须爱护森林,敬畏自然。除了有神灵威慑和祖先规矩,现在更有护林员进行精心的管理。
很自然地,哈尼人很早就知道“可持续发展”的道理,从来都是小心翼翼地不把事物循环发展的链条弄断;他们不自觉地实施的“四度同构”的生态循环模式,与中国传统的“风水”模式很类似;他们对水源地的精心爱护,可以放大为我们对西部“中国水塔”的爱护;他们对林地的理解,与我们今天对森林的理解完全一样。从哈尼梯田文化中,我们能吸取很多的经验。
哈尼人的节日基本上从属于梯田耕作礼仪,既是世俗的节日盛典,又是梯田稻作礼仪,更是对自然的崇拜。每一个节日活动既标志着上一阶段梯田耕作程序的结束,又意味着下一阶段梯田耕作程序的开始,是不同季节梯田耕作程序的转折点,如二月的“昂玛突”(寨神),是春耕季节人们的祭祀活动;六月的矻扎扎(六月年),是夏锄季节的农耕祭祀;十月的甘通通(十月年),是秋收后的庆典性祭祀。
这些祭祀活动,确保梯田稻作农耕的兴盛丰收和传承绵延;也展示了稻作农耕之民哈尼族人民与大自然和谐相融互补的天人合一精神。哈尼梯田并非单纯的物质生产方式,梯田里长出的并非是稻谷,而是哈尼族的文明之树。
活态遗产:把生态农耕文化传播到世界
哈尼梯田是一个活态遗产,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令人震撼的农业景观、巧夺天工的农耕艺术、结构合理的生态系统,对世界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有重要意义。
哈尼梯田的魅力,在于从古至今始终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大系统,不仅是哈尼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源泉,还是“中国人工湿地的经典”“世界农耕文化的典范”。它既不像泰山、黄山等单纯的自然景观,也有别于金字塔、故宫等纯粹的人文创造,而是一个活态的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与自然巧妙结合的奇观。
发现哈尼梯田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是比发现梯田的审美价值更为惊心动魄的一趟旅程。10年前,我归纳了“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哈尼梯田申遗即以此理论作为主要依据;后来我又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哈尼梯田是中国人工湿地经典”,提升了这一理论的内涵和外延;2007年,哈尼梯田成为了“国家湿地公园”。
众所周知,湿地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水源,而且在蓄洪防旱、调节气候、控制土壤侵蚀、降解环境污染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它被称为“地球之肾”。从生态学的意义来讲,红河哈尼梯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性人工湿地的经典性范例,它以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维护自然,优化自然为指归,创造了哀牢山区亘古未有的人工湿地梯田,这一创造丰富、发展了中国的湿地文明。
恩格斯说过: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与民族,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哈尼族(以及红河州各民族),在经济上无法与富裕发达的民族相比,但在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发展这一人类当代最高哲学的思考和表现上,这个贫穷的民族却能够演奏世界农耕文明的第一小提琴,因为哈尼梯田文化所代表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念是无与伦比的。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梯田价值和哈尼族文化如何作出创新性的重构?梯田对于哈尼人来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维系一棵大树存活的根脉。就文化而言,梯田存,则哈尼存;梯田亡,则哈尼亡;梯田兴,则哈尼兴。只有坚持自己的梯田文化,哈尼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何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首先需要有一个文化自觉——把自己民族的文化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上观照、比较,然后决定其存与亡、兴与废;你要为自己的民族找到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和坐标,要为自己的文化作一次命运抉择。
为了这个“文化自觉”,2009年9月,我奔赴美国去拜访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北美代表丹尼尔·古斯塔夫,邀请他来红河参加世界梯田大会。我向他展示了哈尼梯田的价值:地球六分水、三分山、一分平地;这意味着梯地是全球农业文明的一个普遍形态,维持梯地农业因此成为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但目前,仍在耕种的全球梯田,正在日趋减少,譬如,秘鲁梯田,1600万亩中,只有200万亩在耕种;由此,从价值判断上看,中国的哈尼梯田只要坚守下去,就是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
“世界梯田大会,应当是你们联合国粮农组织来召开的,但现在由我们这样一个小民族来举办——我们哈尼人是铁肩担道义,占三尺地,看万丈天。”当我对丹尼尔·古斯塔夫发出这样的邀请时,他说:“我一定要去参加。”
2010年11月11日,“世界梯田大会”在红河州首府蒙自举办,来自世界16个国家的217名专家学者、梯田农民和国际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国际湿地公约组织和美国环境总署等)代表汇聚一堂共商梯田发展。哈尼梯田也因此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全球重要农业遗产”。
在这个国际平台上,哈尼梯田获得了高度评价。菲律宾伊富高原省长、国会议员泰迪巴古勒先生说:“红河哈尼梯田是世界最好的梯田。”联合国粮农组织项目专家闵庆文赞叹:“哈尼梯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令人震撼的农业景观、巧夺天工的农耕艺术、结构合理的生态系统,不仅对本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2013年6月22日,哈尼梯田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我们13年的申遗之路大功告成。哈尼梯田申遗成功,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中国又增加一处世界遗产,更在于它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它以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方式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意义更显独特。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会继续努力,让哈尼族八声部原生态民歌也唱进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家庭中,让古老的天籁重焕荣光。
 哈尼梯田是世界农耕文明史上的奇迹,它呈现出的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良性农业生态系统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景观,正是21世纪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精神。梯田用水是从大沟中挖出无数分支水沟,分支水沟再通到块块梯田中,确保了每块梯田的灌溉。由于山水终年不断,哈尼人的梯田一年四季(除秋收后放干田水晒田的短时间)都注满了水,这水从上一层梯田流到下一层梯田,层层下注,最终又流回江河中,江河蒸发到森林,如此周而复始,永不中断。
哈尼梯田是世界农耕文明史上的奇迹,它呈现出的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良性农业生态系统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景观,正是21世纪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精神。梯田用水是从大沟中挖出无数分支水沟,分支水沟再通到块块梯田中,确保了每块梯田的灌溉。由于山水终年不断,哈尼人的梯田一年四季(除秋收后放干田水晒田的短时间)都注满了水,这水从上一层梯田流到下一层梯田,层层下注,最终又流回江河中,江河蒸发到森林,如此周而复始,永不中断。生态密码:创造了“四度同构”的生态系统
现在元阳县有主干渠(大沟)4653条,截流了全县63958公顷原始森林和次生林中流淌出来的山泉、溪流、瀑布、龙潭水和雨季降落的大量山水,灌溉了境内166689亩梯田和147252亩早地,养活了元阳县36万人口。想要知道“元阳没有一座水库,17万亩梯田的水从哪里来?”答案就在这里。
哈尼人的水利灌溉系统体现了他们与哀牢山地理环境水乳交融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深度与广度在哈尼人居住的村寨设计中也同样展现出来。村寨,是哈尼人躯体和心灵温馨的栖居地,是他们家园的核心,他们在这里出生、成长和死亡,村寨的好坏关系到族群的兴衰。
哈尼人极其重视村寨的规划:村寨上方要矗立着茂密的森林,提供着水利、用材、薪炭之源,其中最神圣的是寨神林;村寨下方是层层的梯田,那里提供着哈尼人生存发展需要的粮食,村寨就设置在这二者之间。
为什么村寨要修建在梯田上方,水源下方呢?这里饱含着哈尼人高度的生命智慧和生活技巧。
因为梯田在大山上,哈尼人收获一粒稻谷要比平原地区的种田人多付出许多倍劳动量。一个平原上的人只要出了门径直走到田里去就可以开始干活,但哀牢山山高坡陡,哈尼人走出家门不是爬坡就是下坎,如果梯田在村寨上方,当人们爬坡上坎来到梯田边的时候,可能已经累得没法挖田了。村寨在上梯田在下,好处就是省力,即人类学家说的“缩短劳动半径”。
对种田人来说,水之外就是肥,“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有许多民族不懂这个道理,种“卫生田”。哈尼人却深知肥料的重要,极善植肥施肥。植肥是在梯田里撒浮萍让它自然成肥,所以春冬季节的哈尼梯田红红绿绿,长满浮萍,犹如织出的花毯。他们很早就懂得沤肥,把蒿枝、紫泽兰丢进田里沤泡成肥。最重要的是施厩肥和野放肥,为此,发明了独一无二的“沟水冲肥法”和“自然冲肥法”,毫不费力就把肥料送到梯田里。
沟水冲肥法哈尼话叫“则克机”,每个村寨都有一到几个宽大的公共积肥塘,牛马粪便污水都贮蓄在里面,经年累月,沤得乌黑发臭,成为高效农家肥,春耕时节挖开塘口,从大沟中放水把它冲入田中。这时的哈尼村寨像过节一样热闹,男女老幼纷纷出动,大家争先恐后用锄头、钉钯搅动黑糊糊的肥水,使其顺畅下淌,沿沟一路有人照料疏导,使肥水一滴不漏地冲入各家田中。
分田到户后,各家各户在房前屋后建起小积肥塘,平时堆沤畜肥,栽秧时节把肥料挑到附近的水沟边倒下去,肥料就顺水一路哗哗哗冲下去。施肥前只需打声招呼,沿途各家会自觉堵上水口,使肥料只冲入自家田中。比起平原地区的农民辛辛苦苦一担一挑地把肥料挑到田里,哈尼人真是高明多了。这样的施肥通常在栽秧前,肥料进田经过翻犁被压入田泥底层,变成了长效的底肥。
到了六七月间稻谷扬花抽穗需要施追肥时,哈尼人家已无畜肥可施,但是他们有“自然施肥法”解决问题。平时各家各户牛、马、猪、羊统统在山上野放,六七月雨水旺盛的季节,大雨自然会把满山遍野的畜粪、腐殖土冲刷下来,这时大沟又发挥了作用,把这些肥水悉数截入冲进梯田。哈尼人此时只需躲在自家的蘑菇房里吸烟筒,大自然已经帮他们完成了施追肥的劳动。
以水的流程为中心,经江边河坝蒸发升空,到高山区凝聚为云雾雨水洒落在森林中,化为山泉瀑布,又流入大沟,由水木刻分流入田,村寨在上,梯田在下,借沟水冲肥,层层梯田成为水的通道,最后水又归复江河。这是天地人三者相合的良性大循环,我将其归纳为“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
这就是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的构成原理,也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依据。哈尼梯田是中国梯田的杰出代表,是世界农耕文明史上的奇迹,它呈现出的良性农业生态系统和独特的梯田文化景观,它所蕴含的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发展的文化特征,正是21世纪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精神。
精神源泉:把梯田当琴弦弹奏生命之歌
梯田不仅是哈尼人的衣食父母,也是他们生活的魂魄,是精神源泉之所在。而那如银链般缠绕大山的条条水沟,那如布匹般包裹大山的道道梯田,正是哈尼人弹奏生命之歌的琴弦啊!
狂热的乡村音乐家——元阳县文化馆老馆长杨叔孔是我的朋友。20年前,他搜集到一首叫做《三弦啊,我的小飞马》的哈尼民歌,爱极了,经常对我引吭高歌:“三弦啊,我的小飞马,弹着你一道一道的琴弦,我的心飞到姑娘身边去了!梯田啊,我的小飞马,踏着你一道一道的田埂,我的心飞到天神摩咪的身边去了!”如歌中所唱,哈尼人是把一道道的梯田作为琴弦来弹奏生命之歌的。
他们对梯田,除了用锄头、犁耙和智慧、汗水,更是用生命来挖掘的。
1000多年前,哈尼人来到了哀牢山,他们所拥有的只是手中短柄的锄头和胸中万丈的豪情。但是,他们把生命的全部统统投放到挖梯田的劳作中,世世代代,从不休止,所以只有他们才能在陡崖上开梯田。
一个哈尼人如何把他的一生与梯田缠绕在一起,我们只要通过两个平常的习俗就可以知道了——
“哦哈都”,意思是“出门礼”。哈尼人的婴儿生下来,第13天才能抱出家门见天地万物,经过这个仪式,天神、地神、万物之神才会正式承认他生存的合法性并对其加以保护,这实际上是哈尼人获得生存权的神圣节日。但奇怪的是,这个仪式全部是指向梯田的。婴儿抱出来的时候,要在家门口立一柄三尖叉,上面挂一顶平时下田用的篾帽和一个挂包,如果是男孩,挂包里要放一把砍田埂用的弯刀;如果是女孩,挂包里就放一把割谷子用的锯镰,然后用3碗糯米饭献天神、地神。
“霍甲霍森森”,意思是“小娃娃开梯田”。这是一种儿童们经常玩的游戏,但它却有专门的玩法和道具。小娃娃们经常爱在自家门前或寨边空地上玩耍,他们每人都有一把小锄头,这种锄头的小巧玲珑跟一把汤勺差不多,当城市里的小孩在玩电动枪时,哈尼人的小娃娃却在用小锄头在地上模仿大人开梯田。
虽然是玩耍,他们和大人开梯田的程序是完全一样的。先开出水沟,还真的把水引进沟里,然后用泥巴筑起一层一层的迷你梯田,再把水引进梯田里去。他们干得非常卖力,不时用小锄头在田埂上拍拍打打,把它弄得滑溜溜的很好看。
实际上哈尼人对田埂的重视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比拟的,“糊田埂”是春耕时每个哈尼男人都要干的活。哈尼人说:田埂是哈尼男人的脸面,做得好田埂的男人,才能获得姑娘的芳心。长年累月,梯田在哈尼男人的手中轻巧起来,飘逸起来,变成了诗行,变成了水墨画。
大人们对小孩子玩开梯田的游戏总是给予鼓励,他们玩得满身泥垢的时候,大人就在旁边眯眼微笑,“梯田”开好后,大人会奖赏小孩每人一个红鸡蛋。这是男孩子的游戏;女孩子则各有一个小笆箩,她们会用小锄头在地上划出一些条条框框代表梯田,然后背着小笆箩在“梯田”里玩拿黄鳝、撮泥鳅的游戏,拿黄鳝、撮泥鳅是哈尼女人干的活儿。
所以,一个哈尼人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把他的命运和梯田联系在一起了,此后他生命的每一程都与梯田为伴——小时候在梯田边游戏;长大后在田棚里谈情说爱;结婚时新娘的穿戴是田间劳动的基本装备蓑衣、篾帽。总之,哈尼人的一生都投放在梯田里了,直到去世,他的坟墓也在梯田边,以便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守望梯田。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比哈尼人更钟情于梯田。他们把所有的欢乐和痛苦都给了梯田,祖祖辈辈,世世代代,无休无止,直到他们把座架哀牢山全部用梯田铺满,包括那些陡峭的山崖。
爱恋产生智慧,哈尼人在崇山峻岭间挖水沟可以证明这一点。水沟,是梯田的命脉,所以只要有水的地方,哈尼人必然要去挖水沟,不管这需要跨越山涧,还是凿开岩石。清代嘉庆《临安府志》里记载,哈尼人到了“水源高者,通以略勺,数里不绝”。就是遇到深涧老箐,就用竹子、棕树这些长直的木材挖成水槽,凌空架起来引水。有时这样的水槽可以绵延数里不间断。
梯田不仅是哈尼人的衣食父母,也是他们生活的魂魄,是精神的源泉。我以为,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将梯田当作艺术品来盘弄的。他们为此倾注的心血、力气和技能并不少于艺术家;他们将梯田视为自己的生命,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梯田。
大山是梯田的家,蘑菇房是稻谷的家。哈尼人从村寨进入梯田,稻谷从梯田回到蘑菇房。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也最动人的来往;而那如银链般缠绕大山的条条水沟,那如布匹般包裹大山的道道梯田,正是哈尼人弹奏生命之歌的琴弦啊!
哈尼梯田是多彩的大地艺术,而实现这一人类创造力、意志力和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哈尼人,则被誉为“大地雕刻师”;“哈尼梯田是真正的大地雕塑,而哈尼人是真正的大地艺术家!”
文明圣树:把梯田当舞台祭祀天地万物
哈尼人把最高的祭祀献给代表寨神的神树,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森林就等于水源,就等于粮食,就等于种族的延续,没有森林就没有水,就不能进行梯田耕作,人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哈尼人的古歌唱道:“有好树就有好水,有好水就开得出好田,有好田就养得出好儿孙。”对哈尼人来说,人的命根子是梯田,梯田的命根子是水,水的命根子是树,他们早已把这一切完整地融入他们的生命和生活。
哈尼人说:“要种大田在山脚,要生娃娃在山腰,要祭寨神在山头。”哈尼人对村寨的环境条件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所有寨子的上方必须有一座山包,上面要有茂密的寨神林,这是哈尼族最主要的公共活动地和祭祀地。崇拜祭祀树木就是崇拜水源,这样也就是对生命之源的保护。
哈尼村寨的建构形成了完整的神林文化,由神树崇拜的物质方式和一套严格纷繁的宗教仪式组成。通常位于较高山头,总管周围几个村寨的“总神林”,位于村寨上方的寨神林,位于村寨左右的神树林,位于村寨下方的“镇压恶鬼林”和村外路边的“人鬼分界林”。
每年农历二月的第一个属龙日,哈尼人都要在一年里的这一天,清洁村寨和各家的门户,举行隆重而盛大的仪式,邀请他们尊敬的神灵——寨神,从大山里进入他们的村寨,进入他们的家庭,进入他们的生活,享受他们的供奉,和他们一起同欢共乐,保佑山寨和哈尼人的平安、富足和幸福。
哈尼族将这一年一度的特殊日子称为“昂玛突”,也就是“祭寨神”的意思。“昂玛突”的历法意义在于由冬季进入春节,冬季休闲结束,春播、春耕季节开始,各支系有不同的叫法和祭祀时间。
今年,在攀枝花乡的洞铺寨我见识了一场最完整的“祭寨神”活动。在寨子后山有一片茂密的森林,森林中有一片巨石环绕的空地,正中生长着一棵高大标直的栗树,这就是洞铺寨的寨神树。
领头的是朱小和。他刻意穿上新衣,包上平时很少包的包头,手握一把弩弓,上面缠着土布,里面包着尖刀。他威严地喝令跟在身后的几个年轻人杀猪、杀鸡、煮饭、献祭。
朱小和是名满元阳、红河、绿春、金平四县的大摩批,他的名字不但中国人类学家熟悉,在日本、美国、荷兰、泰国、缅甸、越南、老挝人类学界也广为人知,他演唱的几万行的哈尼族古歌《窝果策尼果》和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是哈尼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朱小和享有“摩批哈腊”的头衔,“摩批”是祭司,“哈腊”是老虎,这表示他是哈尼祭司中资格最高的人。祭寨神是哈尼族最盛大的宗教盛典,这样的场合只有他才能主持。他端严地率领着徒弟们跪在寨神树下向寨神祷告。
哈尼人信奉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对天、地、风、云、山川、树、石、一草一木都要祭祀,在“天神的儿子”这个自称里,包含着哈尼人对代表大自然的神灵的敬畏与亲近。大树作为森林的代表,也许被世界许多民族崇拜,但没有哪一个民族像哈尼族这样,把大树作为一个族群命脉的精神和物质的至高无上的图腾对象加以崇拜。
哈尼人把最高的祭祀献给代表寨神的神树,是因为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在哀牢山这一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唯一能给他们提供生活用水和梯田用水的就是森林,森林就等于水源,就等于粮食,就等于种族的延续,没有森林就没有水,就不能进行梯田耕作,人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他们必须爱护森林,敬畏自然。除了有神灵威慑和祖先规矩,现在更有护林员进行精心的管理。
很自然地,哈尼人很早就知道“可持续发展”的道理,从来都是小心翼翼地不把事物循环发展的链条弄断;他们不自觉地实施的“四度同构”的生态循环模式,与中国传统的“风水”模式很类似;他们对水源地的精心爱护,可以放大为我们对西部“中国水塔”的爱护;他们对林地的理解,与我们今天对森林的理解完全一样。从哈尼梯田文化中,我们能吸取很多的经验。
哈尼人的节日基本上从属于梯田耕作礼仪,既是世俗的节日盛典,又是梯田稻作礼仪,更是对自然的崇拜。每一个节日活动既标志着上一阶段梯田耕作程序的结束,又意味着下一阶段梯田耕作程序的开始,是不同季节梯田耕作程序的转折点,如二月的“昂玛突”(寨神),是春耕季节人们的祭祀活动;六月的矻扎扎(六月年),是夏锄季节的农耕祭祀;十月的甘通通(十月年),是秋收后的庆典性祭祀。
这些祭祀活动,确保梯田稻作农耕的兴盛丰收和传承绵延;也展示了稻作农耕之民哈尼族人民与大自然和谐相融互补的天人合一精神。哈尼梯田并非单纯的物质生产方式,梯田里长出的并非是稻谷,而是哈尼族的文明之树。
活态遗产:把生态农耕文化传播到世界
哈尼梯田是一个活态遗产,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令人震撼的农业景观、巧夺天工的农耕艺术、结构合理的生态系统,对世界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有重要意义。
哈尼梯田的魅力,在于从古至今始终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大系统,不仅是哈尼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源泉,还是“中国人工湿地的经典”“世界农耕文化的典范”。它既不像泰山、黄山等单纯的自然景观,也有别于金字塔、故宫等纯粹的人文创造,而是一个活态的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与自然巧妙结合的奇观。
发现哈尼梯田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是比发现梯田的审美价值更为惊心动魄的一趟旅程。10年前,我归纳了“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哈尼梯田申遗即以此理论作为主要依据;后来我又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哈尼梯田是中国人工湿地经典”,提升了这一理论的内涵和外延;2007年,哈尼梯田成为了“国家湿地公园”。
众所周知,湿地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水源,而且在蓄洪防旱、调节气候、控制土壤侵蚀、降解环境污染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它被称为“地球之肾”。从生态学的意义来讲,红河哈尼梯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性人工湿地的经典性范例,它以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维护自然,优化自然为指归,创造了哀牢山区亘古未有的人工湿地梯田,这一创造丰富、发展了中国的湿地文明。
恩格斯说过: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与民族,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哈尼族(以及红河州各民族),在经济上无法与富裕发达的民族相比,但在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发展这一人类当代最高哲学的思考和表现上,这个贫穷的民族却能够演奏世界农耕文明的第一小提琴,因为哈尼梯田文化所代表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念是无与伦比的。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梯田价值和哈尼族文化如何作出创新性的重构?梯田对于哈尼人来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维系一棵大树存活的根脉。就文化而言,梯田存,则哈尼存;梯田亡,则哈尼亡;梯田兴,则哈尼兴。只有坚持自己的梯田文化,哈尼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何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首先需要有一个文化自觉——把自己民族的文化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上观照、比较,然后决定其存与亡、兴与废;你要为自己的民族找到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和坐标,要为自己的文化作一次命运抉择。
为了这个“文化自觉”,2009年9月,我奔赴美国去拜访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北美代表丹尼尔·古斯塔夫,邀请他来红河参加世界梯田大会。我向他展示了哈尼梯田的价值:地球六分水、三分山、一分平地;这意味着梯地是全球农业文明的一个普遍形态,维持梯地农业因此成为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但目前,仍在耕种的全球梯田,正在日趋减少,譬如,秘鲁梯田,1600万亩中,只有200万亩在耕种;由此,从价值判断上看,中国的哈尼梯田只要坚守下去,就是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
“世界梯田大会,应当是你们联合国粮农组织来召开的,但现在由我们这样一个小民族来举办——我们哈尼人是铁肩担道义,占三尺地,看万丈天。”当我对丹尼尔·古斯塔夫发出这样的邀请时,他说:“我一定要去参加。”
2010年11月11日,“世界梯田大会”在红河州首府蒙自举办,来自世界16个国家的217名专家学者、梯田农民和国际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国际湿地公约组织和美国环境总署等)代表汇聚一堂共商梯田发展。哈尼梯田也因此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全球重要农业遗产”。
在这个国际平台上,哈尼梯田获得了高度评价。菲律宾伊富高原省长、国会议员泰迪巴古勒先生说:“红河哈尼梯田是世界最好的梯田。”联合国粮农组织项目专家闵庆文赞叹:“哈尼梯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令人震撼的农业景观、巧夺天工的农耕艺术、结构合理的生态系统,不仅对本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2013年6月22日,哈尼梯田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我们13年的申遗之路大功告成。哈尼梯田申遗成功,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中国又增加一处世界遗产,更在于它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它以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方式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意义更显独特。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会继续努力,让哈尼族八声部原生态民歌也唱进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家庭中,让古老的天籁重焕荣光。